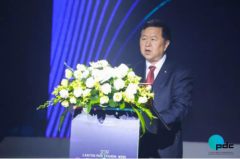2017到2018年间,中国的土地政策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这场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恐怕远远超过更受关注的二孩政策。
故事要从2003年开始说起。从那一年开始,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受到中央管制的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受到了政策的限制。相应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土地供应却受到了鼓励。这种情况在通常的市场经济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在沿海(特别是大城市),收入水平更高,工作机会更好,是人口流入地,相应增加的住房需求本应带来更多的土地和住房供应。但当时的做法,却是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对土地供应施加了更紧的限制,相反,在人口流出的地方却开始建设工业园和住房,后来,还在2009年之后建设了大量的新城。
上述做法,在房地产市场上造成的是严重的供需错配。通俗的来说,就是有需求的地方供给不足,有供给的地方需求不足。人口流出地大量建设新城,导致的是住房空置,严重的甚至整个新城沦为空城鬼城。而在人口流入地,由于建设用地供应相对不足,住房供应增长跟不上人口流入趋势,结果房价快速攀升。
必须要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我们的身体进了城市,但思想还留在农村。中国在40年的时间里,迅速地把城市化率从18%提高到了58%。但是直到今天,大量的人们仍然不理解,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人们更加不理解,进入服务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向大城市及其周围集中是全球共同趋势。在人们的思想深处,仍然认为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其实,即使仍然存在各种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中国已经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至于陈腐的“均衡发展”思想,只不过是人们是把农业社会的人口均匀分布误解成了“均衡”,而事实上,现代经济发展是在空间上高度集聚的,地区间均衡发展是伴随着产业分工的人均GDP趋同。
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在土地政策方面,一开始,先提出了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要能够与人口流动方向相适应,哪里吸纳人口多,哪里得到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就多。到了2018年,终于传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可以跨省域调剂了,也就是说,建设用地指标相对紧缺的人口流入省份可以在支付了调入价格后,向调出地区“购入”建设用地指标。消息来得突然,却是真实的。即便如此,距离我们最早提出这样的政策建议,也已经将近十年过去。未来,一旦这一政策真正落地,那么,人口流入地城市建设用地供应不足的问题将得到缓解。
与此同时,城市群建设的战略已经非常明确,纠正了之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城市发展模式,纠正了片面限制大城市,鼓励小城镇建设的城市化道路。换句话来讲,即便是小城镇发展,也必须是在城市群建设的范围之内,才可能有效。
另一个明确的变化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以此配合城市群的建设,截止2018年已经有九个城市被列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行列。这显示出,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了核心大城市对于城市群建设的带动作用。
但是,改革从来不会一步到位。在建设用地指标能够跨地区再配置的政策变化中,仍然说,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是除外的。这意味着,政策层面仍然要限制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的扩张。从城市规划的传统到决策者的思想意识里,始终认为,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是不能再扩张了,否则,就会带来更严重的城市病。
问题是,城市发展自有其规律。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集聚了大量服务业,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在整个城市的经济总量中占有的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的。相应的,大量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必然集中在中心城区。在全球最为重要的大都市圈已经出现人口再重新回流到中心城区的趋势。
在政策实践上,如果同时降低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又想控制大城市的蔓延,那么,就会出现在大城市中心城区严格限制土地供应的政策。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的超大城市远远未能够向都市圈方向发展。看上去漂亮的中心城市加卫星城模式,似乎符合很多人对于城市发展未来的想象。而实际上,这种模式却伴随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中心城区及郊区之间,甚至在核心大城市及周边中小城市之间,存在大量低效利用的土地。对于一个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大城市来讲,污染的排放本来就不多,郊区大块的绿化用地和农田在环境保护上所做的贡献甚小。而在另一方面,郊区的“绿地”却导致绿化带演变成隔离带,使得核心城区向外的辐射作用受到了阻碍。